据史料记载,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达到了二百多次,单单是东京一座城就发生了四十四次大兴火灾,火灾如此频繁是如何造成的呢?宋朝时期的消防工作又是怎么做到这么差劲的呢?

《宋史·五行志·火》记载了两宋三百多年间的二百多次大型火灾,其中东京城的火灾达到四十四次,位居第一。“内酒坊火”、“相国寺火”、“玉清昭应宫火”、“太平兴国寺火”、“开封府火”……民居,寺庙,皇宫,官府,火,火,火!
火灾频发的原因之一是自然因素,包括雷电和自燃。天圣七年(1029)六月的一场大雷雨,使修了七年的玉清昭应宫“二千六百一十楹”烧为灰烬。至于库房、草场、料物场等地的火灾,则多与堆放物资自燃有关。
原因之二是人为因素。城市建筑分布过于密集,街道狭窄,而茅草屋、砖瓦屋等木结构建筑,几乎遇火便燃。东京城面积五十三平方公里,人口近百万,人口密度即使放到现在也是惊人。更何况当时房屋低矮,人口及建筑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。一旦起火,火势极易蔓延,往往持续一夜都难以扑灭。
火灾的损失总是惨痛的。宋廷不得不加以重视,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加以防治。首先,成立专门的城市消防队,称之为“潜火队”,通常由军队组成。每坊三百步设有军巡铺,在高处修有“望火楼”,专门有人在楼上张望火情。楼下设有“消防站”,内屯百余人的消防队伍和各类救火物品,包括“大小桶,洒子,麻搭,斧锯,梯子,火叉,大索,铁猫儿之类”(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三《防火》)。每当出现火情,专门报火警的快马“望火马”迅速来报,军厢主、三衙军队、开封府潜火队迅速出动救火。
衙门治火的思路有着企业家般的清晰。一,从源头堵。不仅进行严格的灯火管制[“京师火禁甚严,将夜分,即灭烛”(《东轩笔录》),然而夜市和夜禁竟是并行不悖的],并在易发火灾之地采取安全措施。二,设立严格的惩罚措施。那些违法的、放火的、破坏救火的,皆重罚,甚至株连亲属。官员对救火的处理是否得力,也是其政绩考核标准之一。包拯的铁面就曾体现于此。在一次现场救火指挥中,有一无赖上前挑衅干扰救火,包大人二话不说,竟把这厮给斩了(《独醒杂志》卷一)。堵、罚之外,衙门还不忘改革救火方法。比如规定在军队救火之前,邻众也能救火,但整体还是以军队为主。
与火灾同入《五行志》的还有沙尘暴。从端拱二年到北宋末年,京师一带有记载的沙尘暴共计十三次。如端拱二年(989),“京师暴风其东北,尘沙日壹日,人不相辨。”再如淳化三年(992)六月,“黑风自西北起,天地晦暝”;熙宁四年(1071)九月,“京师大风霾”。(《宋史·五行志》、《文献通考·物异考》)
这十三次记载中,以发生在二、三、六月的沙尘最多。北宋前期,沙尘暴多发生于春末及夏季,后期则多发生于春季。这是由于北宋后期气候整体变冷,与蒙古高原产生的气压差降低的缘故。沙尘多由西北风带来,不仅发生在京师,其他地方也有相关记载。就连身在江南的浙江江山县,每年春天都会出现扬沙,当地人称之为“黄沙落。”
至于沙尘暴的情状,与今天并无二致。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曾有诗记载东京的沙尘暴:“红尘昼夜飞,车马古今迹。独怜道傍柳,惨澹少颜色。”(司马光《都门路》),“日射地穿千里赤,风吹沙度满城黄。”(王安石《读诏书》)
梅尧臣专门写有《风异赋》,详细描绘了沙尘暴发生时的情形。那是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,梅尧臣在城外郊游散心,正在一亭舍内休息时,突闻有人大呼,“火来!火来!”听见呼喊的梅尧臣出门远望,试图一探究竟。只见西北方向已昏黄一片,天地之间没了界限,更无从知晓尘土的边际在哪里。过了一会儿,赤色的沙尘和褐色的雾呼啸而至,白天瞬间变成黑夜,风声呼啸大作,飞沙走石不休。人们“莫辩谁何,执手相对”,待天稍亮之后,人们开始结伴返家。那些顺着风走的人脚步几乎停不下来,逆风走的人则奋力行走却仍步履维艰,当时的可视范围只有五六步之内,连城郭的轮廓都几乎看不见了。
不管是火灾,还是沙尘暴,在古代都是了不得的大事。并不仅因为灾害“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”,更是因为气象不仅仅是气象,更是上天的旨意。古人认为,天地万事都能从五行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中得以体现,“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,盈天地之间,无非五行之妙用。”(《宋史·五行》)自汉朝以来,史书里都会有《五行》这一章节,煞有介事地记下五行方面的大事件,对天子起到警示作用。

天之乱,不仅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,有的甚至还直接关系朝廷安危。不但能体现过去的过错,甚至能预示未来的动乱。神乎其神。天禧四年(1020)五月,又是一场沙尘暴发生了:“大风起西北,有声,折木,吹黄尘蔽天。按占并主阴谋奸邪。是秋,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。”(《宋史》)沙尘暴居然能和内侍作乱扯上关系。沙尘暴并不会让当时的人们联想到北方的植被、气候的变化,而是想到天地万物、朝堂上下。在他们的世界里,任何不幸绝不是命中注定,毁灭与灾害带来的病态之美,更不值得去欣赏。类似于奥斯曼帕夏喝着咖啡观火的事,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远观的异域风情。
恐惧。只有恐惧。皇帝作为“天子”,理论上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他所谓的父亲——天。每每当天发生变数时,皇帝方能自发地痛思己过、从善如流(当然也有时刻警醒的明君)。不管大风、大雨、大旱还是大火,都有促使皇帝痛快下达求直言的诏令之奇效。同时,也给了臣子们难得的机遇,能够没有顾忌地指责皇帝。
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,正是梅尧臣《风异赋》里那场沙尘暴发生的日子。风沙只不过持续了一刻钟,“大风昼暝,经刻乃复。是夜,有黑气长数丈,见东南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二六)次日,宋廷却因此停止大宴,并发布诏书,号召各界对皇帝和朝政展开批评。二十七日,宋太宗颁布《大风诸道德音》,内中写道:“而乃霾风示变,昼景中冥。震惧以思,咎谴安执。实繇灵眷,申戒朕躬。”(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一五三)一场沙尘暴,竟能让天子“震惧”,认为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才导致灾难的发生。一如梅尧臣诚惶诚恐地写道:“夫风者天地之气也,犹人之呼嘘喘吸,岂常哉。”风乃天地之气,大风作乱岂能视作寻常事。
沙尘暴不仅能警示天子,也能被政治家拿来互相攻击。据说王安石罢相、吕惠卿得到任命的当天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沙尘暴,飘落在室内席上的尘土一天就能厚达一寸。而雾霾一来,再重大的人事任命也得被取消。庆历二年(1042)九月,宋仁宗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(管理枢密院),宣布任命那天,“黄雾四塞,霾风终日”,沙尘天气持续了一天。朝野上下因此议论纷纷,认为此项任命过重,吕夷简也自行推辞,于是改任为枢密使(兼职)。
火灾与沙尘暴同被列入《五行志》,其不同之处在于事件的主角是人还是天。人犯的错,当然要努力用人力来改变。至于天意,则被天真地相信或被巧妙地利用着。如今我们知道,用避雷针可以逼走天火,在塞外荒漠要多种树。哪怕是冲天大火,朋友圈里却能铺满各自窥见的黑烟轮廓。即使沙尘暴侵袭,仍能淡然地戴上口罩,吐槽的同时庆幸,幸亏是pm10而不是pm2.5。即使至今分析不清雾霾的起因,却多少认为自己能改变什么。
于是忍不住想起那些天真的皇帝和臣子。每当风生火起时,他们总是那么容易惊慌失措,脆弱得让人简直心生怜爱。尽管如此,我们仍思念着那一个“天”,因为有敬畏总不是件坏事。因果循环,谁说不是我们的错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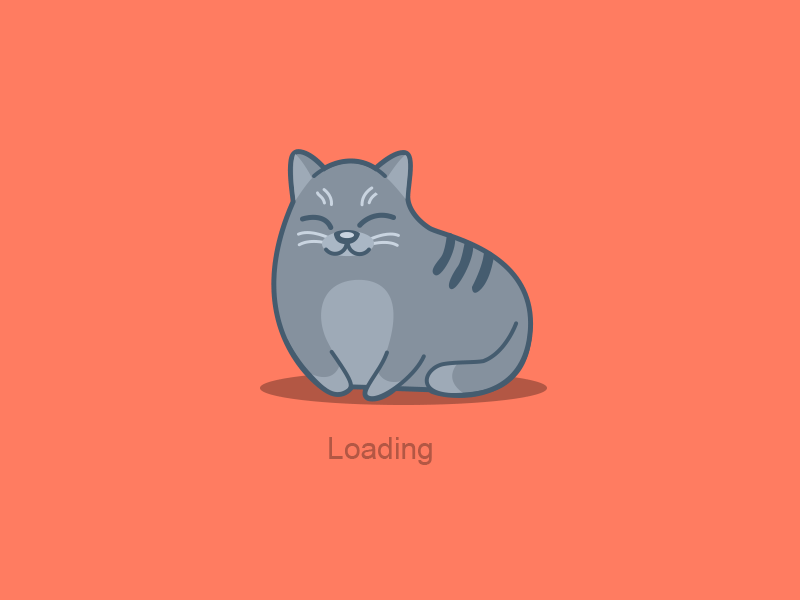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